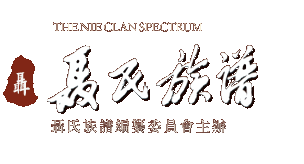来源:聂荣臻研究会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诞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石院子这座院落里。
我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正处于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国家政治上的激烈动荡,各种社会思潮的日益活跃,各派政治力量的争斗,新学与旧学的交替和斗争,所有这些,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汇聚成一股大的历史潮流,封建社会正瓦解,民主主义正在举起。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动,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由于家庭困难,父母把我送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外祖父家距我们家不远,是当地比较富有的一个地主家庭。教私塾的,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沉闷得很。但在外祖父家,也有难得的乐趣。那时,我三舅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法政学堂当时是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一回来,就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倾向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在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我虽然年纪很小,不懂政治,但觉得他们的争论很有趣,对城里来的消息也感到新奇。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尽管搞不清楚,但已经模模糊糊地觉得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就这样,政治需要变革的想法,不知不觉地闯进我年幼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清王朝政府对四川的统治摇摇欲坠,整个四川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
由于四川的富饶,清政府不甘心放过这块肥肉,加上四川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它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但是清政府又深感鞭长莫及,因为四川交通不便,它与外界的主要通道是靠长江,运兵进川和运物资出川,全凭着长江。除长江之外,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了。同时,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是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清朝的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
以后,我听到的就是“保路”运动,这个运动在四川闹得最为轰轰烈烈。清王朝为了侵吞四川民间为办铁路而筹集的巨款,竟然宣布四川的铁路由民办收归国有。这样一来,四川人民对清王朝的愤恨,就像火山一样迸发了,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那阵子,一天几个消息,一会儿听说捉了赵尔丰,一会儿又听说捉了端方,以后又听到把这两个家伙先后处决的消息。当我们听到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心里真是痛快极了!
在这伟大变革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整天在一起议论这些激动人心的大事,老师也不怎么管。在当地,我们最关心的是“同志军”围攻合江。合江知县黄炳燮,凭借合江城三面濒江,城墙坚固,只有西门是陆路出入口,而这里又是高岗,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易守难攻,他坚守合江,拒不投降。“同志军”汇集各种军民几万人,围攻合江几十天,从九月下旬一直打到十二月初,黄炳燮才觉得大势已去,出城投降。但到后来,合江又落到云南军阀手里。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所代替。我也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知识面逐渐开阔起来。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使我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津县立中学(现江津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本世纪初创办的。那时的学制为四年,规模比较大,有好几百人,学生都是住宿生。我进校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班(即第八届)的学生了。
中学时代,我已十八九岁。在这里,我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辛亥革命带着先天的软弱性。革命胜利不久,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复辟称帝,接着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混战,对我的思想触动最大。
江津中学订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包括《新青年》这样的进步刊物。另外,四川虽然交通闭塞,但电报还是通的,各种消息通过电讯传到四川,这些消息又在报刊上广泛传播。我们这些青年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弊,抒发爱国热枕。
签订二十一条以后,大量日本货流入中国,也源源不断地流进四川。处在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所有百货商店摆的几乎都是日本货。这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反感。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正值暑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暑假中,由我们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我在暑假中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遍,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这是我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暑假结束,回到学校,此时,北京五四运动的风暴传到了江津。我们也在学校和江津县城街头集会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我们与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学生联合在一起,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了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我们还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这时,江津县长聂述文出面调停,说是调停,实际上是想压服。谈判的时候,江津驻军团长王天培参加,会场外面站满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聂述文唱白脸,王天培唱红脸,企图迫使学生屈服。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坚持要焚烧日货;商人们则在聂述文、王天培支持下,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当我们得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同学们的愤怒情绪达到顶点,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津中校长邓 仙(此人是国民党员)、学监李耀祥、罗中林百般阻挠,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准上街。我们一二百名学生,一气之下,冲出校门,串连其他学校的同学,游行到“文昌宫”,将日货搬到河边,全部烧毁。这样一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我们下毒手。很显然,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在学校是再也待不下去了,待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也是促成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为,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自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说服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少年气盛,一怒之下,就不考虑后果如何了。
在中学时期,另一件对我影响很深的事情,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它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在四川,也是大小军阀混战不已。有个军阀叫刘存厚,长期盘据川北,一直到我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到川北建立根据地时,才把它消灭。四川军阀有个特点,因为交通不便,经常是关起门来打,需要的时候,联合客军打对手,客军就是云南、贵州的军阀。而四川军阀自己则从来不打到外省去,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富有的缘故。
在兵荒马乱之中,各地成立了许多民防团,大多用以自卫。在我们江津,也成立了民防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回研究四川武斗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同志听后笑了起来。
军阀们打来打去,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尤其是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但是,那时我很年轻,看不清楚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总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好办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更增强了我 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少有这种印象: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成立了工农政府,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改良主义)也夹杂其间。尤其是无政府,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比较大,但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许多道理我还弄不太懂,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没有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到的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能解决问题。进步思想界提倡反对封建,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向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些我都是赞成拥护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一九一九年秋,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去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据最近不完全统计,江津一县就去了三十多人。我约了几个同学,先到了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办法。事先我们知道四川有两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我们到重庆是想打听一下,究竟是经过预备学校好,还是直接去法国好,再就是了解一下去法国的手续、费用等具体问题。在重庆得知留法手续很简单,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只要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在预备学校又主要是学法文,大家商量说,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到法国学法文,比在国内学效果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我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舍不得我远离家乡,担心我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去法国。自己去法国,要一大笔钱,家里穷,就靠我几个亲戚帮助,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这样,我和十来位同学怀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馆那里办了护照。
从此,我一别故乡,就是三十六年。一九五五年我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的情况,才重新回到时常思念的故乡。回到家乡,真是思绪万千。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朋故交已经去世,我默默地思念他们,但最使我思念的,是那几位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乡同学。那次回家,我到了江津中学,一到学校,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吴平地等烈士的形象,立时浮现到我的眼前。他们在学校时就追求进步,关心时政,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切磋琢磨。吴平地同志牺牲得最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文基础很好,一九二○年北上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捕牺牲。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同志也于一九二○年前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中钟汝梅是与我一路走的,一九二一年还一起在法国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学习回国,他也到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苏省军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贺龙同志的部队中。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听到这两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的消息。我站在校园里,默默地缅怀着几位先烈,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为我的母校哺育了这样几位先烈而感到自豪。现在,江津第一中学已经为他们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纪念先烈,教育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