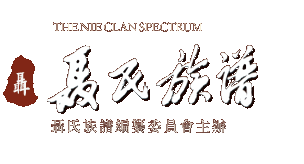刊登于《上海滩》2000年10月号 作者:宋路霞

聂家后人九十年代聚会合影:
前排左起:聂光墉、聂光墉夫人俞惟瑛、聂光崎夫人任永恭、聂光墀夫人夏蟠寿、瞿强立
后排左起:聂光来丈夫梁秉钧、聂光珏、聂光来、聂光禹、周麒、聂光秀、聂崇训、聂崇实
四老爷斗胆冒犯袁世凯
聂管臣(其炜)是聂家第二代中的四老爷,在聂家开创恒丰之初,与老三聂云台共掌家业,后来因兄弟间意见不和,就退出了恒丰。适逢北方的实业巨头之一孙多森邀其北上,遂离开了上海来到北京,后来又到天津,是我国银行界的老前辈。
孙多森是当年光绪皇帝老师孙家鼐的侄孙,与其兄孙多鑫,均是以袁世凯为后台的北方实业的创始人。辛亥革命后,他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就邀请聂管臣出任副总裁。孙多森其时还兼任着安徽省都督,政界事物繁多,常不在北京,中国银行的日常行务,实际由聂管臣一人主持。1915年年底,居然还冒犯了袁大总统。
那天他正在行里上班,突然接到财政部的电话,要他去中南海进见袁大总统。他奉命前往,晤谈片刻,袁世凯就对他说:“我现在急需四百万现款,你赶快给我准备一下,拨给财政部入库备用。”聂管臣一听,觉得这事不能照办,因为中国银行并不是你官办银行,而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动用这样一笔巨款,须得召开董事会才能决定。于是就对袁说:“我在行里仅是副总裁,这么大的事,是否可叫总裁回来,跟董事们打个招呼再办。银行有董事会章程在,我个人实在无法从命呵!”袁世凯一听此话,立马把脸一沉,他没想到聂管臣居然敢顶撞他,于是冷冷地说:“那好吧,你们不能办我叫别人办去!”聂管臣随即退出。
没想到第二天财政部就送来一封信,内称:
“着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管臣)即日离职,前往京沪考察金融,旅费得向中行出纳支取三千元。”聂管臣阅后付之一笑,觉得老袁无聊,第二天便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也未去领那所谓的车旅费。
事隔三个月,报上刊登了袁世凯做皇帝的消息,聂管臣才恍然大悟,原来袁说的“急需”,就是为了筹备登基做皇帝呀!他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没有摄于权势,助纣为虐。又过了两个多月,消息传来,袁世凯不仅皇帝美梦已成泡影,连他老命也保不住了,仅做了83天皇帝梦,他的“圣旨”一张也没走出过中南海,就一命呜呼了。
聂管臣只身北上救“中孚”
聂管臣退出中国银行后,孙多森也辞了职,北洋政府中粤系得势,梁士贻当上财政部长。孙多森又创办了中孚银行(1916年),自任总经理,亦请聂管臣出任协理,该行总部设在天津。
这期间,由于业务上处理方法和用人观点上的不一致,孙、聂之间曾发生不小的矛盾,以致于聂四老爷一气之下,愤而返沪,这样总行就空缺了协理。不巧的是,孙多森因政事家事急火攻心,于1919年病逝了。这样一来,“中孚”就出现了总理、协理同时出缺的局面。这就为孙家在北方实业界的对手、同为安徽人的周学熙集团(两江总督周馥的后代)找到了借口。周学熙召集了当时在天津的安徽籍人士商议,决定由启新洋灰公司的代理董事长龚心湛(字仙舟,时为中孚银行董事)出面,推派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李士鉴(字希明)率领若干人马到中孚银行,企图乘机接管。
可是凡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时孙多森的长子孙震方正在津浦铁路局任出纳员,年纪虽轻但亦知此事非同小可,中孚银行将大权旁落了,于是急与其十三胞叔孙多钰商议,拍急电去上海,催请聂管臣务必立即赴津主持行务。聂管臣在此关键时刻还是念及孙家的旧情的,于是欣然北上,坐到了总经理办公室。等到李希明等接管人马到行,发现聂氏已在主持行务了,大为惊讶,一时尴尬得无地自容,只得诺诺而退,回向龚心湛复命。龚心湛当年任汉口中国银行经理时,聂管臣曾以中国银行副总裁的身份赴汉口视察,算起来还是聂的老部下,对聂的为人也深有了解,此事遂不了了之,中孚银行的一场危机就此化险为夷了。
这位四老爷办事一向沉稳,精于计算,在为孙家服务的几十年中,颇多为之谋划。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孙家的事业中心也由北方迁到了南方,在上海成立了通孚丰联合办事处(总管孙氏家族的诸多企业和中孚银行),时孙多钰任总经理,亦拉着聂管臣任协理。后来由于孙家自身矛盾太多,孙多钰返回了天津,聂管臣就辞职告退了。
有一天,聂家四小姐聂其璧在一家理发店里碰到孔祥熙。孔祥熙当年与聂云台都是青年会里的干部,相处很熟,就问及三哥可好?四小姐说,三哥生病在家,不能出来做事了,四哥身体挺好,正赋闲在家。孔祥熙知其人才可用,就在中央银行安排了个稽核处副处长的职位,还配备了轿车出入,直到日本人打进租界,中央银行被日本正金银行接管为止。当时日本人劝他留下来为日本人做事,他坚决不从,就此开始了后半生的寓公生涯。
白相人阴谋敲诈一场空
被聂家后代称之为六老爷的是聂潞生(其焜),是继聂云台之后恒丰纱厂中期的总管,二十年代末,还曾与一帮企图敲竹杠的白相人,相见于法庭。
那时日本人已在上海、青岛等地开设了很多纱厂,他们的设备和技术都超过中国纱厂(丰田式布机已压倒了英国和德国的机器,以至于英国人买了丰田式机器去仿造),同时资金雄厚,周转灵活,因此成本低,质量好,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使得申新、宝成、统益、振泰、恒丰等纱厂大受其苦,产品积压在纱布交易所内达一万多包,成为投机商“踢皮球”的筹码,纱交纱价不断下降。
当时申新厂的荣宗敬最着急,因为那时他的纱锭最多,受影响最大,因此主张纱厂帮要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复兴公司,将这批积压的“烂污纱”收买出清,活跃交易。当时参加的只有五个厂的代表,申新厂代表荣宗敬、溥益纱厂代表徐静仁、大丰纱厂代表徐庆云、统益纱厂代表吴麟书、恒丰纱厂代表聂潞生。大家推聂潞生为负责人,因为他是纱交所的发起人。
这个复兴公司于1928年8月成立,半年时间内,出清了一万多包仓栈积压纱,使市场价上升到合理的价格,这对正当的纱商来讲是有利的,可是对于那些投机商人来说,尤其对于专门依靠这批积纱进行抛空的客户来说,是挖掉了他们赚钱的根子,于是激起了一些流氓的怨恨。恰在此时,又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投机商乘机兴风作浪,故意哄抬纱价,而五方代表中有一方又违反了协议,暗地里将出清的“烂污纱”重新在上海市场上卖出,这就被白相人抓到了借口。他们推张啸林出面,勾结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薛岳,派军法官专审这个案子,可是审来审去,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原来该军法官是个广东人,对江南一带方言听不懂,而且语文程度也不高,第一堂叫名字时,把聂潞生叫成“摄”潞生。聂潞生只好不吭声,后来又问道:“你叫的摄潞生,是不是就是我聂潞生?我姓聂,不姓摄。”这一下把个军法官弄得脸红脖子粗。
白相人请的律师叫朱榜生,一口苏州话。第一堂先叫荣宗敬,荣一口无锡话。此两个人的话,法官一点都听不懂,第一堂只好不了了之。第二堂问徐庆云,徐是一口宁波土话,法官又是听不懂。第三堂问董仲生,董是一向讲不来话的,讲起来期期艾艾且不得要领,军法官仍是无从下手。
第四堂才轮到聂潞生,幸好此六老爷会讲普通话,因此可以跟军法官直言相对,反正军法官只能听懂他的话,他就趁机大发议论:“中国纱厂不能保本,我们复兴公司想挽救这个局面,怎么能说我们操纵市场投机呢?”当时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不久,各地抵制日货正风起云涌,聂潞生亦大做文章:“我们这是振兴了中国的纱厂,试问法官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抵制日货?是不是应该振兴中华民族?”直说得那法官连连点头。而轮到白相人请的苏州律师讲话时。他唠唠叨叨的讲了许多,法官仍是一句不懂,只好又不了了之。
后来上堂后,军法官总是先叫聂潞生讲,聂潞生一讲总是一篇大道理。后来一堂一堂地过去,白相人看看苗头不对,就在第十堂上由苏州律师说:“此事误会了,诉讼可以撤消,不过要被告拿出2万两银子来,补贴我们的诉讼开销。”原来他们想敲诈100万两银。后来退到50万两,实在站不住脚了就退到2万两。可是由于聂的坚持,结果一个铜板也未让他们捞去,案子也无形中结束了。
狂风暴雨中的“旧王孙”
全国解放,对于聂家这样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大家族来说。实在无异于一场狂风暴雨。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司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无不时刻深刻地、从各个角落彻底地改变着聂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的巨变的家族。
在这场巨变中,聂家有一部分人是积极跟上了社会的步伐的,他们努力改变着过去的自我,以适应新的环境,年青一代也努力摆脱家庭的思想包袱,积极上进,立志不再为家族接班(公私合营后也无家族的班可接了),而要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聂光堃(含章)积极经办了恒丰纱厂的公私合营,合营后改为丝织厂,他即随之从一个棉纺专家而转为丝织专家,出任经理。厂里仍有好几个聂家人“留守”:聂光琦为副厂长、聂光尧为福利科长、聂光墉为供销科长,聂光来是厂里医生。其他人如聂光达、连翰安夫妇,是中山大学畜牧兽医系和中央大学园艺系毕业生,解放后响应政府技术人员归队号召,放弃了待遇优厚的中纺公司工作,投身艰苦的市郊农业战线,数十年如一日,作出不少贡献,成为高级专家,聂光达晚年还被推选为市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聂崇泗、聂崇实、聂崇训、聂崇志、聂崇正、聂崇嘉、聂崇慧等均先后考入全国名牌大学,个个都是学业尖子。聂崇实在复旦大学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聂崇嘉在交大本科毕业后,到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攻读研究生,在苏联著名教授指导下继续深造。
然而聂家毕竟是个在上海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家族,有着牢固的“洋务”传统,从老太爷聂缉槼开始就与洋人打交道,办洋事,在江南制造局内聘用了上百名洋技师、洋职员、洋译员,著名的传教士傅兰雅的夫人还充当了聂云台、聂管臣的家庭英语教师。同时崇德老人曾纪芬又信基督教,与洋牧师多有交往,每年圣诞节都请牧师到家里来举行仪式,孩子们大大小小地都被叫出来唱圣诞歌,孩子们读书也从小都在教会学校读书。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包括艺术观点、仪表风度,无不已渗透了他们的肌体。更何况聂云台、聂管臣都曾是青年会的积极分子,还担任过总干事等职务。孩子们长大了只要能考取,总是送他们去留洋……在这样一个东西交汇、华洋细胞“杂处”的古老而现代的家族里,他们的血液里已积淀了几代人的洋务细胞,而面对五十年代那种视西方的一切均为洪水猛兽的社会格调,他们该如何把握和相处呢?
于是他们中就必然有一部分人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奈。
那天笔者坐在聂家崇字辈的一家客厅里,年轻的主人顺手就拿出一张1928年的法国明信片,图片是法国的一座小城市的街景,黑百色十分古朴,背面有法国朋友写的两行字。这可能是他们爷爷辈的遗物,被混在一堆照片里而幸存于今,现在他们谁也讲不清这明信片的来历,也不知是谁的法国朋友了。但他们很明确地说,过去家里这类“洋货”很多,西洋唱片、图片、世界名著等。孩子们常被带到淮海路一带的私人花园里出席派对,在一起谈论的也都是“海外风云”,崇拜的人物不是大科学家即是大文学家、音乐家,或是大探险家、大侦探……甚至还设法到傅雷先生家里借外国名著看。
八十年代末,老七房的聂崇立,已在美国芝加哥一所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他稍有点积蓄,便把老爹老妈聂光尧、杨佩珊接了过去,让老两口好好游览一下异国风光。他原以为老人出入语言上有不便,想不到父亲竟能用流利的英语跟美国人交谈,这令他大吃一惊!他在想,是什么力量使父亲把自己“包藏”得如此严密呢?以至于几十年来,作为儿子竟不能真正了解父亲?!还有一次,孩子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老掉牙的外国唱片,和一架只有78转的手摇式唱机,那唱片放出来的是巴赫的《圣母颂》,大家正听得入神时,父亲光尧却止不住泪流满面地走开了。人们谁也不敢想象,那优美而圣洁的旋律,是如何重重地触痛了他那尘封的往事,谁也讲不清,恐怕连他自己也讲不清那眼泪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
他们理智上很稳定,认为新社会好。因为解放后,人人生活有保障,消除了战乱,根除了地痞流氓和娼妓,真正禁止了鸦片,扫荡了社会上的污泥浊水……然而要他们亲自实践眼前新的一切,他们似乎又难以完全默契和适从。旧社会和新社会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于是他们就变得日益胆小怕事起来。
聂光堃不等十年浩劫的到来,早已把家里的老照片、旧帐本、信札、纪念物统统处理干净—这当是他老人家的先见之明,因此没有给后代带来抄家的麻烦。然而现在麻烦倒来了,因为大家要写文史资料了,后代们为拿不出老太爷当年的照片而着急万分。聂光墀是交通大学的教授,因热心公益活动而被推为工会小组长。后来想到自己尚在拿恒丰纱厂的定息,这样能算工人阶级吗?担任工会小组长合适吗?这可是个大问题,应当向组织上汇报清楚。结果一汇报,他的小组长就给“撤”了。聂光琦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革命之“火”还没烧到他头上,他就早早地打点家当了,送的送,卖的卖,把南昌大楼内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赶紧上缴,识相地躲进一处仅20多平米的旧房……
倒是家里的“下人”和小字辈们比他们要勇敢—造反派叫家里的老佣人吴妈起来揭发主人聂光尧,吴妈愤怒地吼道:“我们家大少爷(光尧排行七房老大)早就是共产党了!吃饭都是叫我这老太婆一个桌子上吃的,没有他我这老太婆早就翘辫子了,叫我揭发他什么?!”聂光琦的女儿聂小琦,“文革”后几次三番申请到日本去自费留学,单位的某领导硬是扣住不放。聂小琦怒从中来,那天正好手上端着一碗粥,那么就照准那脑袋上扣过去……
聂崇平“文革”中因讲江青的坏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单位里监督劳动,打扫厕所。别的“反革命”星期天不敢休息,而他却偏要休息,而且背起汽枪到乡下去打鸟。他说:“反革命归反革命,反革命也是人呀!”单位里领导斥责他,他与之争辩,领导辩论不过他,气急败坏地掷下一句话:“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你这样的反革命!”崇平则恨恨地以牙还牙:“现在就叫你看看!”
“吃”下的定息再“吐”出来
1961年的一天,正在上海民用设计院工作的聂光禹,被单位叫进一间会客室,说是政府找你谈话。他有些莫名的紧张,坐定后才知来人是法院的干部。那干部说:“你们家的恒丰纱厂现已定为‘敌产’,国家决定予以没收,所以原订的定息现已停发,但是你们过去已拿过好几年定息了,现在要求你们全部退还国家,希望你能配合政府,做家里人的工作,尽快把已领取的定息还出来……”
聂光禹一听头皮都有些发麻,他那时年轻气盛,不解地问:“我们家是民族资产阶级呀!怎么一下子变成‘敌产’了呢?”
那法院干部人很诚恳,如实地告诉他:“是根据一位老工人的检举,说是你们恒丰纱厂在抗战前经营不善,向银行借了很大一笔贷款。抗战爆发后,你厂在日伪统治下,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这是利用日本人的势力还清了前欠,如果日本人不来,你们也无法还清债务。所以说,恒丰厂应是人民的财产,应该归还人民。”
聂光禹仍是不明白,关于抗战中日本人强行加入恒丰股份的事情,解放后的“肃反”和“三反五反”中不是都查清了吗?“三反五反”中恒丰厂还被评为“基本守法户”呢,怎么如今又变了呢?法院干部最后劝他,不要有什么想不通了,还是做做家里人工作,配合政府赶快把这件事做好吧。
聂光禹回家后一打听,果然各房各户都收到了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说是有人检举恒丰厂是敌产,立即停发定息,并将进行公诉,审讯等等。
这件事在聂氏家族中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事隔50年后,人们看到一张当年法院的判决书,那上面果真印着:“根据一位老工人的揭发------”然而为什说恒丰是敌产,日本人究竟加入了多少股资,中国人占有多少股份,其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也就是说,把恒丰定为敌产的依据,并没有讲明白。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决定了的事情就必须执行。但是聂家毕竟已拿了五年的定息了,大家庭要生活,孩子要读书,有的家庭还有“存货”,有的老早吃也吃掉了,用也用掉了,有的家庭缺乏劳动力,是靠定息过日子的------那么道理也很简单,“吃”下去的定息,必须再“吐”出来!于是聂家就忙成一团,有存款的到银行提取存款,没有存款的把金银首饰作价抵充,实在拿不出的只好借债。至此,恒丰纱厂完全成了国营厂。
最近笔者听说,聂家有一位远亲在中南海里工作,负责保管毛泽东同志的遗物。她在毛泽东同志收藏的大量照片中,发现有曾纪芬老人八十大寿时,聂家大家族的合影照片,不知是谁送给毛主席的。这么说来他老人家还是关注过聂家或是曾家后代的情况的,可是1961年,不知他知不知道聂家在上海发生的事情。
不过聂家人还是弄不明白,当年荣家的申新厂和郭家的永安纱厂,也被日本人加入过股资,为什么他们没有划为敌产,而单单聂家的恒丰厂划成了敌产?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经过那么多运动都没有说是敌产,而且上海经济研究所还为恒丰厂写过专书:《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认为恒丰是典型的民族资产,而到了六十年代初,却成了敌产呢?如果说恒丰的某些个人参加过敌伪棉纱组织,那也是个人的事情,而恒丰是股份制的厂子,大家族在曾纪芬在世时就已分家了,为什么要牵连到整个大家族呢?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聂光禹曾斗胆写过一封要求复查此案的“上诉信”,但没有回音,又写给北京有关单位,仍无回音。他索性跑到北京,找中央统战部上访,接待人员很认真地听了他的诉说。又过了一段时间,上海法院通知他说,法院已接受了复查的要求,将进行调查处理,但直到现在,仍不知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