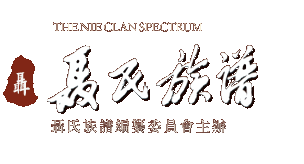原载《上海滩》2000年7月号 作者:宋路霞

黄浦江边的聂家福地
黄浦江在上海地图上走了个“3”字,曲曲而北。在它绕过陆家嘴折向东去的北岸,即现在的许昌路、杨树浦路、辽阳路、霍山路一带,从前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因为清末有一任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的家园及其主要的私家企业,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聂缉椝(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是晚请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在沪期间,他先是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重用,于1882年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会办(副总经理),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八年,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主动联络水陆各军,以水雷加强上海港的防务,昼夜巡逻不殆,沪上人心乃安。他又延请傅兰雅等西方技术顾问,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有力地保证了前方所需军火的供应。中法之战中国获胜,他的名声亦为朝廷上下瞩目。在他的主持下,这个连年亏损的“国营特大型企业”还甩掉了连年亏损的帽子,扭亏为盈,他卸任时还盈余十几万两银子。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继续看好他的才干,在晚年两次举贤不避亲,以“才大心细,精檄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等语,向朝廷保奏这位亲侄女婿。不久,聂缉椝又荣升苏松太道。至此,从他走出湖南衡阳起凡14年间,已从一个湖南滇捐局的帮办,步步跃为华洋杂处的上海滩的“党政军第一把手”,位列封疆,可谓一路青云,成为湖南聂氏大家族中,最大的“高干”。
这片地面上有两处聂家花园,一处在霍山路(旧称威赛路),俗称“聂公馆”,是聂氏早期在沪的家园(更早一些时住在江南制造局内和上海道道署),方圆不足三亩地,据说绕有亭台之胜,可惜现已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只见高楼拔地而起,直逼云天,已是教苑宾馆和霍山路小学的所在地了。只有大门口花坛上堆积的几块太湖石,据门房间的老师傅说,那是当年道台花园的旧物。
另一处是在辽阳路亚明灯泡厂的马路对面。长长的一条街面,南达惠民路,北接霍山路,面积足有几十亩地,现已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各式民居。而当年里面只有五幢旧式三层的红砖房子和一个网球场。所有的亭台、花园和池塘,都用高高的竹篱笆圈围着。篱笆的尽头是一家香烟厂,男孩子们调皮,在篱笆上掏个洞,可爬到香烟厂去偷香烟牌子。大些的孩子喜欢打篮球,所以网球场又可用来当篮球场用,以至于后来竟诞生了一个“崇德”聂氏家族篮球队,常在报端登出赛事。近年聂家有一外孙女名张心漪(台湾前财长费骅的夫人)在海外撰文回忆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由此可知,这是一处中西合璧的、相当现代的海派园林,这是在聂缉椝之后,他的三儿子聂云台主持家政时的杰作。他把聂氏家族在沪的近百口人均安排于此,每天大门口车马成群,冠盖如云,男人们忙于做生意、办企业,女人们忙着陪婆婆,上教堂,管孩子,串门子。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是聂家最为兴旺发达的一段时期。
现在这儿的花木、竹篱笆自然早已不存,而那五幢红砖房子居然依然完好无损,只是风光不再,旧燕未归,只能任其七十二家房客的“新旗”上下飘扬了。
花园南侧不远的黄浦江边,屹立着当年聂家的骨干企业:恒丰纱厂(解放后改为第三丝织厂,现又改为XX公司),数十亩江边滩地上,有五组雄伟的厂房,中心地带一组“长”着锯齿般的房顶的红色平房,据说是该厂最早的一批厂房。现在人们走进车间,迎面依旧机声隆隆,盈尺之内对话亦需大声喊叫。这原是清末最早的大型纱厂之一。
当然,从聂家花园里走出的名人亦不少,除了道台大人之外,还有他的妻子曾纪芬(世称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六小姐,聂氏家族的精神楷模),他的三儿子聂云台(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总经理),六儿子聂潞生(恒丰纱厂中期总经理),孙子聂光堃(聂含章,恒丰纱厂后期总经理),四子聂其炜(中国银行协办、中孚银行行长),七子聂其贤(清末湖南武军司令官、武字黄统领、省防守备队司令官),女婿瞿宣颖(瞿兑之,著名作家、古典文献研究学者、前清军机大臣瞿鸿機之子),女婿周仁(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科技大学名誉校长、中科院冶金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媳妇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曾国藩慧眼识快婿
聂家原本清代衡山望族,以三代进士、两代翰林,以及乐善好施知名远近。
其祖先乐山公(聂继模)在清初天下初平时,还仅是衡山城西一家小中药铺的老板,但他教子有方,本人诗书终生不离手。他以下三代连出三个进士,继而功名不断。他本人所做的《诫子书》被收入《皇清经世文编》。按说这是部专收清廷高级文武官员著作的大部头书,而他以一布衣身份亦能跻身其中,足见其名声不凡。其次是他的善名,他有个自我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实行义诊,不仅对来店抓药的贫民义诊,还主动去县监狱为犯人们义诊、送药。后来他的儿子当了陕西省镇安县的县官,他老人家80多岁去陕西看儿子时,仍不忘老传统,仍在初一和十五去该县监狱送诊送药,也许他认为清廷所关押者多为穷人的缘故吧,可见其为犯人们服务是终生制的。
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亦为进士,并点了翰林,散馆后外放广州各地当县官,长达30多年。他继承其祖先的乐善好施的传统,每到一地,总要捐助建育婴堂、牛痘局、清节堂(为清苦寡妇而设)、宾兴馆(资助贫士考试而设),这些善举深受当地百姓称颂。作为当时湘军首领的曾国藩决意把满女(湖南人称小女儿)嫁给聂家的,还是因为聂家老太爷秉公办事,亲自制止了一场血洗事件的义举。
同治九年(1870年),聂亦峰在广东新宁县当县官。这个县的西村是个大村,只有两个姓氏,即余姓和李姓,二姓比邻而居。余姓有丁口约万余,而李姓有丁口约二万。然而余富李贫,余族出举人、贡生、监生很多,还有两三个人在外省做官。而李姓人家只知耕地种田,文武两庠绝无一人。可能是由于山水地形的关系,李姓人家出入总要从余姓人家的地皮经过,世有俗嫌,因此两姓之间就常有“荫注砍伐诸事涉讼公廷”。每次打官司,总是余胜李败,大概与官府里有没有人大有关系。
这年李姓中有个叫李鸿钧的,因在省城开设制糖作坊赚了钱,花钱买了个武科举人的第一名,第二年因病要回家乡。李氏家族因从来没有科举上的光荣,这回来了个武举人头名,被视为为族争光,于是大开祠堂,盛设仪仗,龙灯鼓乐,迎之归祠。孰料途经余村时惹起余姓的嫉妒,余姓人围上来设法阻扰。他们先是诡称“贵人骨重”,需用一杆秤秤其斤两,竟从轿子里将李鸿钧拉出来,捆入竹筐内,挂上秤钩,然后把一只狗牵来作为秤砣,并且将之高挂在三只木架上,大庭广众之下加以凌辱。一时笑声震天,然后一哄而散。当时李姓人家的大队人马正集中在李姓祠堂里,兴高采烈地等待轿子到来,忽闻此种暴行,一时群情激昂,火冒万丈,拿刀动棒,冲入余村,决一死战,竟酿成空前惨烈的大械斗。余姓死者七百余,李姓死者一千二,尸横河岸,十三里许,腥血污秽,河水皆臭……这么一来,李姓积恨未申,徒逞血气之勇,不仅旧仇未报,死者反而倍于余姓。而余姓自知理亏,深恐官厅追查,于是汇集了30万元至省城运动,由一古玩店老板柯老六,转托当地制军瑞麟的门丁诸天章,上下行贿,反告李鸿钧谋反。瑞麟制军拿到贿赂,遂派出地方官聂亦峰与水师统领黄某,率部队前往围剿李姓。令下三日,瑞麟又增派部队包围了李村,一场更大的惨案迫在眉睫。
聂家老太爷聂亦峰是多年的地方官,当然明知个中原委。他大义凛然,亲自到第一线,说服各路将领万不能开枪,不许部队擅入李村;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叫李鸿钧出来到案陈诉。俟李氏一到,即刻真相大白。然而瑞麟制军令下不容改变,一再下令围剿,而聂亦峰五次抗命不从,坚定不移,宁可罢官回家。事后他真的在家闲居了两年,而那场灭绝李姓的围剿终于被制止,余李二姓的积案亦未刑一人而得了结。
……这个事件传入曾府令曾国藩大为动容,于是决定把最小的女儿曾纪芬许配聂家,广东巡抚蒋以沣亲自为之提亲。聂家公子聂缉椝长得一表人才,生平好经世之学,虽无科举之名,然秉公办事,乐善好施酷似乃父,正是曾家意中的女婿。只是当时曾老太爷已经病重,未及看到满女成婚。1875年,聂缉椝和曾纪芬在曾国荃的主持下,结为伉俪。
多事之秋的海上地方官
从1890年到1911年清廷覆没,因晚清政局的动荡,上海道也走马灯似地更换,20年间竟换了17任道台,平均一年多换一任,最短的任职期仅一个月,而聂缉椝任上海道在1890至1894,四年整,是为任职期较长的一位,仅次于他的一个老乡袁树勋(海观)。
然而这几年正是多事之秋。他一上任就碰上了他的老土地,江南制造局2000多工人的大罢工。原因是新任总办刘麒祥将每天工作8小时延长为9小时,工人们不干,于是罢工。新任道台面对新任总办及2000名旧属,真是左右为难,只好两头做工作,最后以总办这头允许增加饭费为条件,终于使工人们恢复了上工。
1890年,座落于黄浦江边杨树浦一带,占地300多亩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总算开工投产了。这家清末最早的官督商办的机器棉纺织厂,经过十几年的反复筹备,吸收公款及商股共一百万两,拥有530台织布机,雇用工人4000名,终于开门大吉,开始赚钱了。谁知好景不长,开工刚两年,一场大火把厂子烧得个精光。北洋大臣李鸿章忧心如焚,急责盛宣怀到上海,会同聂缉椝抓紧重建。盛宣怀出政策,允许中国商人开办纺织厂(在此之前只许官办和官商合办),条件是出纱一包,捐银一两,直至把织布局的官款赔清为止。聂缉椝负责具体落实,南北舟车,千辛万苦,终于在大火后不到一年,在旧厂基上又开新局,建成了华盛纺织总局。这个新厂有织布机1500台,纱锭六、七万枚,规模大大超越先前,加上裕源纱厂和华新纺织总厂的纱锭,使上海拥有了近10万枚纱锭,约占当时全国的76%。
不多久芜湖又出教案。当地农民烧教堂,掘教士坟冢,暴尸于旷野。当地官员把为首的农民抓了起来,但法国主教不满意,串通法国领事向清廷施加压力,不仅索赔巨款,还要划出两块地皮,归其永久性使用。事在安徽久议不决,两江总督移案至沪,请聂缉椝来解决这一难题。聂道坚持款可赔而地决不可给,因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西洋各教在国内传播甚广,各地屡有教案迭出,如任教主漫天要价要地,日后岂有中国人立足之地!于是援中外此类案件处理惯例与法国领事磋商,据理力争,终于以2500两银予以了结,法国人无如不可。
他任职沪道的最后一年,又撞上了甲午海战。他原本于1893年已升任浙江按察使,将去赴任时,前任沪道邵友濂奏请朝廷,认为海防吃紧,台湾方面战事将一触即发,上海为供应、运输饷械之战略要地,绝非平庸之辈能够胜任,请求将聂缉椝继续留位,务必保证台援为要。当时邵友濂任台湾巡抚,正在积极作战争的准备。况且沿海一带几为日本船只所封锁,海道艰险,聂缉椝亲自部署严加防范,将江南制造局生产的种种军械,源源不断运到台湾。第二年战争果真打响,浙江全省戒严,浙江巡抚廖寿丰急电上海,要聂缉椝立即前去赴任,督办海防……
甲午战后和议已成,苏州和杭州成为新的开放城市。朝廷命他督办杭州通商商务条约,他在谈判中力争捕房、管路完全主权,使各国列强无计可施。然而 苏州的商约却经岁未决,清廷又命他为江苏布政使。浙江巡抚廖寿丰见他要走,又急忙秉奏朝廷,请求留他署浙江布政使……于是,浙江、江苏、安徽,他已“三权藩篆”矣。
“聂家子孙再也不要做官!”
俗话说树大招风,聂缉椝官做的大了,在战争时期或是国事繁难的时候,有朝廷的重托,无人敢以诽词。然而天下已定,风调雨顺,各种内部矛盾就会渐趋表面化,至使聂大人盛极转衰,大受其害。
十九世纪末叶,聂缉椝正在浙江巡抚任上。浙江一省担负了战争赔款每年达百万元,不堪重负,于是动脑筋开发财源。他发现铸制铜元获利甚厚,于是剔除各种杂乱货币而以颁布新型铜元为流通货币,一年下来,居然赢利上百万。
此时,浙江有一巨商高某,仪仗财势,胆大包天,居然把浙江金华、衢县和黄岩三地的矿产私自售给意大利商人,又通过官府中的种种关系,买通商务局委员,窃取了商务局的关防大印,作为官府已批准的证据,而实际上商务局的总办并未知晓此事。矿产卖出后,高某大获其利,引起浙人哗然,群起争执,并派出代表与意大利人同上北京,告到总理衙门交涉。朝廷下令由浙抚聂缉椝查办。
高某为浙江豪富巨族,神通广大,与朝廷某大员属儿女亲家。聂大人调查此事颇费周折,后来终于弄清了事情原委,秉直呈报,揭出此中重重黑幕,然而那贪官也不是好惹的,继续制造假象,欺骗舆论和朝廷,聂大人屡次予以据理驳正。结果,朝廷宣布废除高某与意人的商约,把商务局总办另案革职,高某亦受到查处,谁知此一大快人心之事,却成了日后的祸根。那帮黑势力想方设法要把聂台整下去,以报一箭之仇。
1906年夏天,聂缉椝自觉心神疲惫,精力不支,两次奏请回家休息,然而朝廷不准。
八月,御史大夫姚舒暗中收集了密报,向朝廷参他一本,说他在铸新铜元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于是朝廷下令查办。奇怪的是办案人员并没有查出他的舞弊营私的证据,拖至数月,仅以任用私人回禀朝廷,所谓查无实据,然而仍罪不可赦。朝廷一向重用、信任聂缉椝,这回不知被什么风吹斜了耳朵,遂下令将他开缺,即去职回家。
聂缉椝一方面阿弥陀佛,“欣然色养”,总算可以逃脱官场世纲,可以回家休息了;另一方面觉得自己一生尽忠朝廷,最终却被所诬,如此灰溜溜地回家,实在意气难平。于是告诫其子孙:“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亦工亦农的治家方略
聂缉椝毕竟出身于忠厚的诗书之家,从小受的是农业中国的传统熏陶,对泥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官场上呆久之后,就更加厌恶都市的尘嚣氛围,所以一旦有了一些积蓄之后,他便要回到老家去,置办农田,种稻种棉,过几天清闲日子,而把上海的产业交给他的三儿子聂云台和四儿子聂其炜去打理。
回老家置办农田也是需要资本的。这个原始积累的基地,仍是在上海,主要靠恒丰纱厂。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厂始终是聂家的命根子。直到现在,聂家还有好几个人在该厂拿退休金。
聂缉椝在湖南长沙建有很大的宅院。而在上海,最初住在江南制造局厂区内,后来可能为了照应恒丰纱厂,才把住宅建在该厂附近威赛路(现霍山路)。他没有眼红租界内的繁华,家眷在他生前,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长沙,所以威赛路上的住宅仅有“巴掌大的一块”。在沪上豪官巨贾纷纷看好租界,并且向西部发展的时候,他仍老老实实地呆在原地。那时盛宣怀和邵友濂的家园选在静安寺路,花园大得可以踢足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住宅亦从安庆路迁到了西区华山路;李经羲则筑庐跑马厅以西,现在是62中学所在地;刘瑞棠、陈夔龙等封疆大吏亦在公共租界建有豪宅。相比之下,他那三亩地,直如一座小土地庙。
然而他的工厂在他的儿子手里办得挺出色。在最初朝廷尚不许私人经办纱厂时,他就采取“附股”的形式,“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取名华新纺织总厂,亦属于官商合办的性质。188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当时的上海道龚照瑗及以办盐务起家的大财主严信厚(字筱舫)筹办。聂缉椝是1890年当上沪道之后参加进去的。于1891年开工,资本45万两,至1893年,已发展为拥有纱锭15000枚,织布机350台的大厂。当初作为官商合办的织布厂,已有上海织布局在先,那么为什么还要另外再办一个官商合办的织布厂呢?现在从“商”的一方的投资者来看,其更象一家由地方高级干部投资的“三产”,名义上是“附股”,而实际上是独立的,大概是李鸿章给这些“割头兄弟”的一种照顾吧。
这个厂在甲午战争之前营业情况较好,甲午战争之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和挤压,开始连年亏损。1904年,聂缉椝派出自己家的帐房先生汤葵生,由汤葵生及聂云台用复泰公司的名义租办该厂,情况才有了好转。谁知第二年汤葵生就去世了,大权就全归聂云台掌握。聂云台雄心勃勃,重新改组复泰公司,用借来的巨款买下了该厂三分之二的股份。1909年租约期满,他再次向私人贷款,其中向袁海观(亦任过上海道)就借贷5万。买下了全部股份,至时使该厂成为聂家的独资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然而聂家欠下的袁海观的钱,直至聂缉椝去世前一年才还清。
聂家在湖南老家买田的气魄并不下于在上海买厂。1904年,聂缉椝用华新纺织新局的盈利,在洞庭湖边大规模地围湖造田。先是在南州淤田地带买得四万余亩,又陆续收买邻近刘公垸一带的湖田一万余亩,组成了聂家的领地:种福垸。这片湖田东西长十六华里,南北宽十华里,总面积达五万余亩,可称一个超级大庄园了。可是新围起来的湖田,秋冬季看起来挺好,一到夏季湖水暴涨,弄不好就遭了淹,所以必须高筑堤岸,年年加固。盛夏季节各处都要派人巡堤以防塌方,所以虽然在年成好的时候,能收租谷五六万石,收棉花一万多斤,然而用于修堤固堤的费用亦非常之高。到抗战的时候,种福垸的堤坝上已高出湖面十米,宽度可跑小汽车了。由于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亦住在这片土地上,为安全起见,聂家又组织了“保警队”,有武器装备,某种程度上,这五万亩湖田已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
或许是聂家老太爷有先见之明,这个种福垸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确实给聂家子孙带来了福气。他们一旦在上海的生活有了问题,或者碰上了战乱,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向这块根据地靠拢。抗战时期上海的聂家子弟卖掉了辽阳路的大花园,有的躲入租界避难,有的就躲进了种福垸。那时种福垸里甲鱼横行,在场院或田间小径上随时可以用脚踩住它们的背壳,抓回来煮了吃。至今聂家的子孙们还有人说,聂家的老人们大都高寿,曾纪芬活到90岁,李敬萱活到96岁,曾宝荪活到94岁,现在还有一位住在万体馆附近的聂家老人亦是90多岁。活到80岁的根本不稀奇,大概就是当年在种福垸里吃甲鱼吃多了吧! |